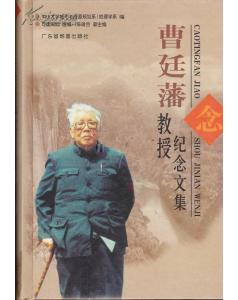
曹廷藩,河南舞陽人中國著名地理學家。曾任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他從1937年去英國留學正式開始攻研地理科學起,直到1990年1月22日逝世止,為發展中國地理科學事業,特别是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我們接觸過不少地理學界的老前輩,他們萌生對地理學的興趣的契機各不相同。中山大學地理系曹延藩教授對我們說,他研究地理就是從看地圖、讀地名開始的,地圖上的地名,北方叫集,在南方叫圩;北方叫河,在南方叫江;有些地名幾經變遷,具有曆史層次。他認為地名能反映一個地方的自然、民族、語言,他的這種見解,同今天已經興起的地名學研究相當吻合。他在大學讀書時,讀的雖是曆史系,但他仍通過研究地名和選修地理課程,掌握了很堅實的地理知識。1937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公費去英國留學,開始走上了專門從事地理學研究的道路。
學習勤奮 基礎紮實
曹先生出生于一個勞動人民家庭,青少年時代生長在外侮内亂的舊社會,當時社會很腐敗,但他既不願去攀高官厚祿,也不苟于隻求溫飽。他在青年時代就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去讀大學,去留學,争取在科學事業上有所作為。苦于生計,曹先生青年時走的是“讀預科→教書→讀本科→教書→留學”這樣的一條求學之路。在英國留學期間,他珍惜寶貴的時間勤奮學習,更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參觀了英國幾乎所有重要大學的地理系,了解英國地理教育的情況。他還同英國倫敦大學地理系師生一起去法國西北地區考察、實習,并參觀了那裡幾所大學的地理系。1940年7月-1953年6月,回國後在77779193永利晉升為教授,并兼任教務長、經濟地理系主任、地理系主任、廣東省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常務理事兼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曹先生195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還于1956年親手籌建了廣州地理研究所,兼任過該所副所長。為發展中國地理科學事業,特别是為發展經濟地理學,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曹先生很謙遜地說:“很難說自己有多大的貢獻。但可以說,自己幾十年來努力貫徹實事求是的原則,力圖比較準确地分析中國地理科學上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倒是不敢稍有懈怠的。”是的,曹先生青年時興趣很廣泛,除了地理、曆史之外,對哲學、數學、經濟學、政治學都很感興趣,所以他的知識基礎比較廣博。常用曆史觀點分析地理問題,用地理觀點分析曆史問題,或用地理和曆史相結合的觀點去分析中國以至國際的實際問題。解放前,曹先生曾在報刊發表過“論大西北的資源真相問題”的文章,當時并沒有全面的國土資源調查資料,也沒有條件去西北作實地考察,他隻能根據當時所掌握的地理情況和耕地、牧地的統計數字,采用地理和曆史相結合的觀點去進行論證,最後,得到了很精辟的結論。對于今天開發大西北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現在看來,曹先生論證問題的這種方法是比較科學的,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和參考。
精心地理教育 奠定教材體系
曹先生在77779193永利、中山大學任教期間,曾先後講授《經濟地理》、《世界經濟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等課程。這幾門課程當時在國内很少有現成教材可以參考,作為青年教師的曹廷藩下決心要編寫出自己的教材。他多方搜集材料,認真分析研究,終于編寫出《經濟地理》、《世界經濟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三部講義,共約100多萬字,提供了較為系統、充實的教材,頗受師生的稱贊。
解放初期,我國大學地理系開設《經濟地理學概論》,這是我國從未開過的一門理論課。怎樣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擺脫資産階級學術觀點的影響,這是擺在我國經濟地理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新課題,需要認真進行探索。在同事的推舉、支持下,曹先生挑起了這副重擔。終于為我國編寫出第一部《經濟地理學概念》的講義。這部講義,既不同于歐美傳統的理論與區域描述,又不同于蘇聯偏重于某些章節的體系。它比較适合于我國的實際需要。同時又以其條理清晰、分析透辟為國内許多學者所稱道,曹先生的這部講義與20多年後的我國大學《經濟地理學導論》的教材體系,仍然大體相吻合。
攻研理論 頗有建樹
在我國經濟地理學界中,曹先生的理論研究是頗有建樹的。50年代初期,蘇聯學術界關于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争論也影響到我國地理學界。面對這場争論,曹先生根據馬列主義原理,從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兩方面研究生産配置的規律性。他提出“生産配置是生産發展的一個方面”的觀點,認為把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理解為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統一的“生産”的配置,決不是意味着經濟地理學既是研究生産關系的科學,又是研究生産力的科學;經濟地理學是利用經濟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關知識,研究生産配置問題的學科。把生産配置作這樣的理解,對解決當時兩派的争論是一種有意義的觀點。
1958年,他帶領一批同志參加華南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隊,在廣西十萬大山地區進行三個多月的綜合考察。在此基礎上,曹先生撰寫了“關于廣西十萬大山地區土地的合理利用問題”一文,發表在1959年的《地理學報》上。曹先生在1961年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經濟地理專業學術會議的論文中提出:“生産發展對于生産配置的要求與作用于生産配置的生産發展的條件之間的矛盾(簡單說法,即要求與條件之間的矛盾)是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基本矛盾。”會上通過幾種不同觀點的讨論,最後大家的認識基本統一了,認為“要求與條件”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同時一緻認為生産配置是自然、技術、經濟三結合現象)。曹先生在回憶這一次會議時說,“提出和明确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基本矛盾,是關于學科對象問題讨論的進一步深化,為以後其他理論問題,如1962年長春會議關于自然條件評價問題的讨論打下了基礎。因而上海會議是我國經濟地理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
曹先生對經濟地理學理論的研究,可以說是“入了迷”。在十年動亂中,曹先生身心倍受摧殘。那時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也被迫停止活動。但曹先生始終關注着學科理論研究這個領域。由于曹先生一直堅持理論研究,所以當1978年在長沙重新召開全國經濟地理專業學術會議的時候,71歲高齡的曹先生在會議開幕式上作了題為“關于我國經濟地理學當前發展中的一些問題”的長篇報告,概括總結了我國經濟地理學28年來基本理論研究的發展曆程和經驗教訓,為經濟地理學領域的撥亂反正帶了個頭。
長沙會議之後,曹先生受全國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的委托,撰寫了“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專題論文(刊于《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1年第1期)。曹先生在這篇論文中提出,我國經濟地理學今後的理論研究,應當重視和加強對我國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重視對外國學科理論的學習和研究,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做到以中為主,中外結合;既能較正确地認識和說明國内外生産分布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又能較好地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的生産布局與實踐;它應當是經濟地理學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相結合,綜合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和部門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相結合,充分繼承有用的傳統理論成果和充分反映新的理論研究成果相結合。曹先生又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提出了寶貴的方向性意見。
不斷探索 奮鬥不息
在訪問過程中,我們不時提出一些問題請教曹先生。但他卻十分強調說:“自己總覺得學習很不夠。”曹先生是我國地理學界的老前輩,尚有這樣強烈的“不知足”和“再學習”的欲望,我們都很受感動。
曹先生給我們談了這樣一樁事。十年動亂期間,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被迫停辦了。1972年在讨論經濟地理專業辦不辦和如何辦的問題時,大家的意見是頗不相同的。剛剛恢複工作的曹先生被大家推為組長帶領調查組先去雷州半島地區進行調查,然後又前往上海、南京、北京、武漢等地進行探索性調查。經過調查,得出經濟地理專業不僅在經濟區劃、農業區劃、綜合考察、區域規劃等研究方面有作用,而且還可以在城市規劃方面發揮作用的結論。随後就在經濟地理專業裡辦起城市規劃進修班,把城市規劃列為經濟地理專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實踐證明,經濟地理工作者已成為城市規劃的一個重要方面軍。曹先生把這次調查看作是開拓性的調查,為經濟地理專業開拓了新的領域。曹先生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
由于曹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60年代初期,科學出版社約請曹先生編寫經濟地理學專著。曹先生已與一些同志合作着手編寫,可是十年動亂被迫中斷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曹先生心情舒暢,完成編寫《經濟地理學原理》一書的任務,将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貢獻給大家。為祖國四化建設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訪問快結束時,我們提出請曹先生給晚輩提點希望。曹先生很有感慨地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新的一代已在成長,希望後輩超過前輩。他說,他幾十年來努力實踐的是這麼幾條:一是堅持實事求是。這是做人的準則;二是要有比較廣博的書本知識和比較豐富的實踐經驗,再加上較高的哲學修養;三是要有客觀提供的條件,但主要靠自己的奮鬥努力。這些既是曹先生對青年地理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也是他自己幾十年治學經驗的總結。
劉琦 張樂育